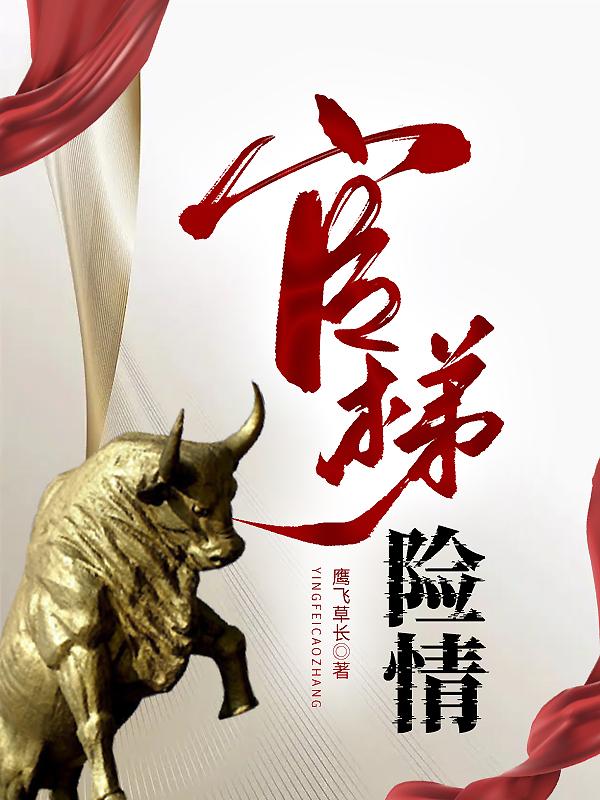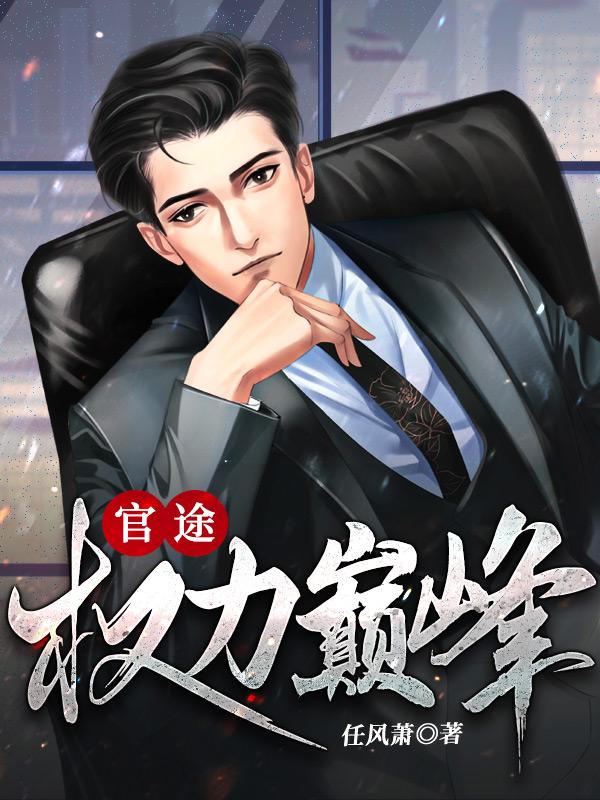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574章 血炼(第3页)
第1574章 血炼(第3页)
>“今天也有人在等你。”
>不需要回复,不必负担。
>就像夜晚的灯塔,
>它不指引方向,只证明存在。
做完这些,他长舒一口气,望向窗外。
雨势渐歇,乌云裂开一道缝隙,月光如银纱般洒落在远处山巅。那光并不耀眼,却足以照亮前行的路。
抵达县城已是次日清晨。林小满拖着疲惫身躯入住招待所,刚躺下便接到周医生来电。
“阿枝昨天去了坟地。”声音带着罕见的波动,“她坐在奶奶墓前,嘴里一直在念叨什么。邻居听不清,可她说……她说自己在‘说话’。”
林小满坐起身,心脏怦怦直跳。
“你能确定?”
“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发声,”周医生顿了顿,“但她嘴唇一直在动,手里攥着你给的那支觉醒笔。最奇怪的是……笔尖有轻微磨损痕迹,像是真的写过字。”
林小满猛地睁大眼。
觉醒笔的工作原理是捕捉使用者意念中的语言信号,直接转化为数字文本存储于云端。若笔尖出现物理磨损,说明……有人强行用它当作普通书写工具!
这意味着??阿枝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写字”,哪怕神经损伤让她无法控制精细动作!
他立刻请求周医生拍下笔身磨损部位的照片并发来。同时调出觉醒笔的云端数据日志。当他看到最新一条未上传成功的本地缓存记录时,整个人僵住了。
那是一段长达十二分钟的“书写”轨迹,虽无实际字符生成,但脑电波活动曲线呈现出清晰的语言节奏模式:停顿、重读、情感起伏……完全符合人类倾诉时的心理节律。
换句话说,阿枝确实在“说话”。
只是她的语言,不在声带,而在笔尖;不在空气中,而在数据流里。
林小满双手颤抖着回复:“请务必保管好这支笔。我会尽快安排技术人员进村,做一次现场适配调试。”
挂掉电话后,他在日记本上重重写下:
>语言从来不止一种形式。
>哭泣是语言,绘画是语言,
>甚至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呐喊。
>而我们所谓的“治愈”,
>不是教会别人如何像我们一样说话,
>而是学会听懂他们本来的声音。
接下来三天,他奔波于省城各大高校与科技公司之间,终于说服一支神经工程团队加入“忆璃计划”的公益协作网络。他们同意免费为阿枝定制一套“意念书写增强系统”:通过头戴式传感器捕捉她大脑语言区的微弱电信号,结合觉醒笔进行动态校准,最终实现“心想即成文”。
项目启动会上,一位研究员问他:“值得吗?只为一个可能终生无法言语的孩子投入这么多资源?”
林小满平静回答:
“你们研究的是技术能否识别语言,
而我在乎的是??
这个世界,是否愿意承认一种不同形式的‘说出’。
如果连这点耐心都没有,
那我们的文明,不过是一群聋子围坐在扩音器旁,
吵嚷着‘谁在说话?’”
会议结束当晚,他收到阿枝的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