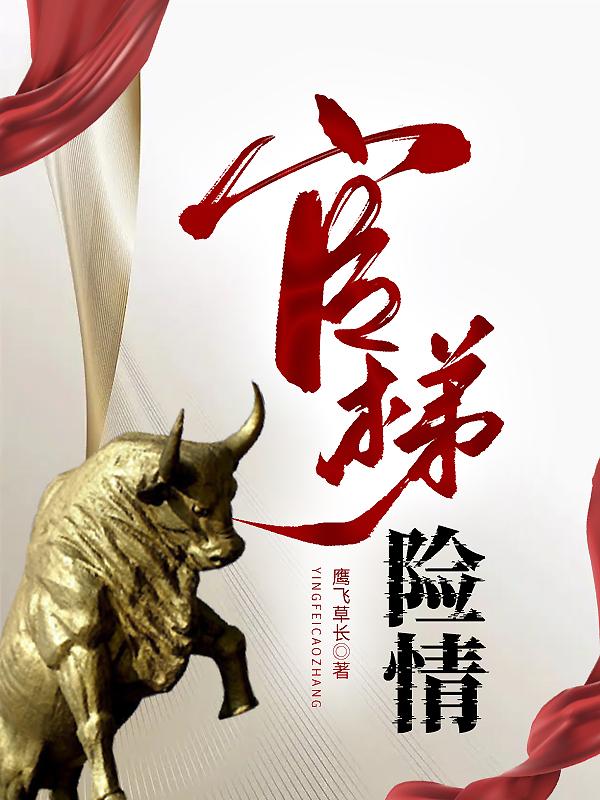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61章 宫里来信(第2页)
第461章 宫里来信(第2页)
>若有一天人们把我供起来,那便是我真正死了。”
柳芸的眼泪无声滑落。
她终于明白,所谓“守碑之道”,并非守护石碑本身,而是守护那些不愿被美化、不敢被遗忘的真实。陈七一生拒受封赏,拒绝入史,甚至临终前烧毁所有战报档案,只为守住一句话:“这条路不该因我而被人记住,而该因走过它的人被记住。”
可人世间总有人渴望神明,于是便造神;总有人恐惧虚无,于是便填以谎言。冥枢虽败,但它种下的种子早已生根??那便是人类对“意义”的贪婪。
数日后,柳芸召集忆学馆弟子,在原万忆塔基座上立起一座无名碑。碑面光滑如镜,不刻一字。她当众宣布:“此碑不为纪念某一人,而为提醒所有人:当我们急于铭记时,请先问一句??这是真的吗?”
消息传出,民间议论纷纷。有人赞其清明,也有人斥其冷酷。“连陈七都不配拥有名字?”一名老兵怒闯忆学馆,手持断刀,眼中含泪,“他救过我们全营!他背伤员走过心渊峡谷!他修的路至今还在用!你凭什么说他不该被记住?”
柳芸静静看着他,良久,才开口:“我没有说他不该被记住。我说的是??不要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她命人抬出一口旧箱,打开后,全是这些年各地送来的“陈七遗物”:一把据说是他用过的佩刀,一支写满兵法的竹简,甚至还有半块印着龙纹的玉佩……她逐一拆解,揭穿伪饰:刀是新铸,竹简墨迹未干,玉佩出自宫廷库藏,根本不在边关出现过。
“这些都不是他。”她说,“他是那个在雪夜里默默铲雪的人,是那个替死去工友写家书却不敢署名的人,是那个把功劳让给下属、自己蹲在角落啃冷馍的人。”
老兵怔住,手中的刀缓缓垂下。
柳芸又取出一份泛黄的手稿,正是《守路日记》的抄本??原来那夜失踪的孩子并未死去,而是逃入深山,将书藏于岩洞之中,临终前托付给了猎户后代。辗转二十年,终被送到忆学馆。
她当众朗读其中一段:
>“阿音走那天,我没哭。我不敢哭。我知道,只要我一哭,就会撑不住。我会扔下这条路,追着她的马车跑。可我答应过要守到最后一日。所以我只能把她缝的那件军袍穿在最里层,贴着心口。每次冷得发抖,我就摸一摸它,就像她还在身边补衣服。”
全场寂静。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颤巍巍站起,哽咽道:“我……我是当年修路队里做饭的王婆。我记得那件袍子。左袖破了,她用蓝线补了个梅花。她说……她说男人粗手笨脚,补不好,让我帮她。”她掏出一块布巾,展开后,竟是一小片残布,上面依稀可见一朵褪色的蓝梅。
柳芸接过布片,与手稿对照,分毫不差。
那一刻,许多人哭了。不是因为悲壮,而是因为真实。他们终于看见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陈七,而不是高坐云端的神像。
就在当天夜里,那颗悬于空中的星辰突然闪烁三次,随后缓缓下沉,落入忆河之中。河水泛起碧光,涟漪扩散至全国忆碑。凡是触摸碑石之人,皆见一幕景象:陈七独自坐在长城残垣上,望着夕阳,手中握着那柄铁铲。阿音的身影悄然浮现,坐在他身旁,轻轻靠在他肩上。两人没有说话,只有风吹动衣角,远处蓝莲花开遍山坡。
画面消散后,所有忆碑表面浮现出同一句话:
>“我愿平凡地活,也不愿虚假地永生。”
翌日清晨,柳芸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粗糙,笔迹稚嫩,像是孩童所书:
>“姐姐,我在庙废墟里找到了一块石头,上面画着两个人,一个拿铲子,一个缝衣服。我还捡到一枚铜扣,像是军袍上的。我不认识他们,但我梦见他们叫我‘小石头’。我把它带来了,放在你门口。”
>
>“我想,有些人就算没人记得,也会一直活着吧?”
柳芸推门而出,果见台阶上放着一只麻布包。打开后,是一枚锈蚀的铜扣,和一块绘有简笔人像的石板。她抚摸着铜扣,忽然发现内侧刻着极小的字:“赠阿音,戊申年冬,陈七。”
她抱紧布包,久久伫立。
与此同时,远在福建渔村,那位老妇人的孙子正趴在海边礁石上画画。他不会写字,只会涂鸦。画中有两个小人,一个高些,拿着铲子,另一个矮些,手里牵着一根线。背景是屋子,窗内亮着灯,屋外风雪交加。
他把画放进一只空陶罐里,埋进沙滩,还插了根小木棍做标记。
“奶奶说,这样就能传得很远。”他对同伴说。
“可没人会挖出来啊。”
“总会有的。”孩子认真地说,“就像她找到铜牌一样。有人会想起,然后继续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