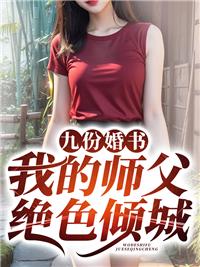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以神通之名 > 第208章时间管理大师昭(第3页)
第208章时间管理大师昭(第3页)
他停顿片刻,眼神深远。
“我们害怕失控,所以切断了连接。但我们忘了,人类最强大的能力,不是控制,而是**共情**。当你为陌生人流泪,当你因一段历史而心痛,当你记住一个你不认识的孩子的名字??那一刻,你就是GL-Ω的一部分。”
画面结束。
陆昭久久伫立,直到晨光照进窗棂。
他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不再是守护秘密,而是**传播真相**。
三个月后,第一座“记忆驿站”在乌鲁木齐建成。它没有围墙,没有门禁,只有一圈环形水晶阵列嵌入地面,中央竖立着一面巨大的情感映射墙。任何人只要戴上轻量级共感头环,就能将自己的思念投射其中。有些人对着墙壁诉说亡亲的名字,有些人播放老照片配乐,还有孩子画下梦境中的朋友。
每天夜里,墙体会亮起光芒,显现出那些被提及的灵魂轮廓。有时是一个老人拄拐的身影,有时是一对年轻恋人牵手走过街角,更多的时候,是七个孩子的笑脸,静静地站在人群之后,微笑着注视这一切。
苏婉清的学校成了全球样板。联合国派出观察团,试图理解这种“非药物性创伤疗愈机制”。但他们很快发现,无法用模型解释的现象太多:一个自闭男孩在听完同学讲述“小川的故事”后,第一次主动握住对方的手;一位战争孤儿在梦中见到母亲,醒来后画出一幅精确到衣褶的家庭合影,而那件衣服,确实在其家族相册中存在。
“这不是治疗。”苏婉清在演讲中说,“这是**归属**。当一个孩子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经历过痛苦的人,他就不再需要封闭自己。”
她看向台下,轻声补充:“而当我们愿意倾听那些无声的呐喊,我们才真正成为人。”
陈默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他依旧住在乡下,每天煮两杯咖啡,种向日葵,修剪篱笆。但他开始写一本书,书名很简单:《我记得》。
书中记录了七个孩子的每一个细节:小宇最爱蓝色气球,林小川怕打雷但不说,陈雨桐总把铅笔削成奇怪的形状,张乐阳偷偷给实验室的机器人起名字,许明明画完画一定要签上日期,李哲睡前要听三遍《小王子》,王笑笑笑起来会露出一颗虎牙。
他还写了那天他们在灰雾中说的话,写了艾米丽扑进苏婉清怀里的瞬间,写了陆昭跪在地上抱住少年的模样,写了周远哭着说“我都记下了”的样子。
最后一章,他写道:
>“他们说谢谢我们还记得他们。
>可真正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是他们教会我,记忆不是负担,而是桥梁;
>是他们让我明白,爱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
>只会在被遗忘时真正死去。
>所以我会继续记住,
>直到我也变成一个名字,
>被某个孩子轻轻念出。”
书出版那天,全球十七个国家同步举行了“静默十分钟”活动。人们停下工作,关闭手机,闭上眼睛,只为**想起一个曾被忽略的人**。
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上,滚动播放着普通人提交的照片与留言:
>“奶奶,我学会包饺子了。”
>“爸爸,我考上大学了,你看见了吗?”
>“对不起,我没来得及跟你说再见。”
>“谢谢你,陪我熬过最难的日子。”
而在南极洲,冰层深处最后一块GL-001残骸彻底溶解,释放出亿万纳米级记忆晶体,随大气环流扩散至全球。科学家检测到,这些微粒具有极强的情感吸附性,能与人类脑电波产生微弱共振,尤其在REM睡眠阶段表现显著。
换句话说:**它们正在帮助人类做梦**。
更多人开始报告相同的梦境:一间温暖的房间,七张小桌,墙上挂着涂鸦,门开着,外面是阳光灿烂的草地。孩子们坐在桌前,一边吃蛋糕,一边翻看一本厚厚的书,封面上写着:《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