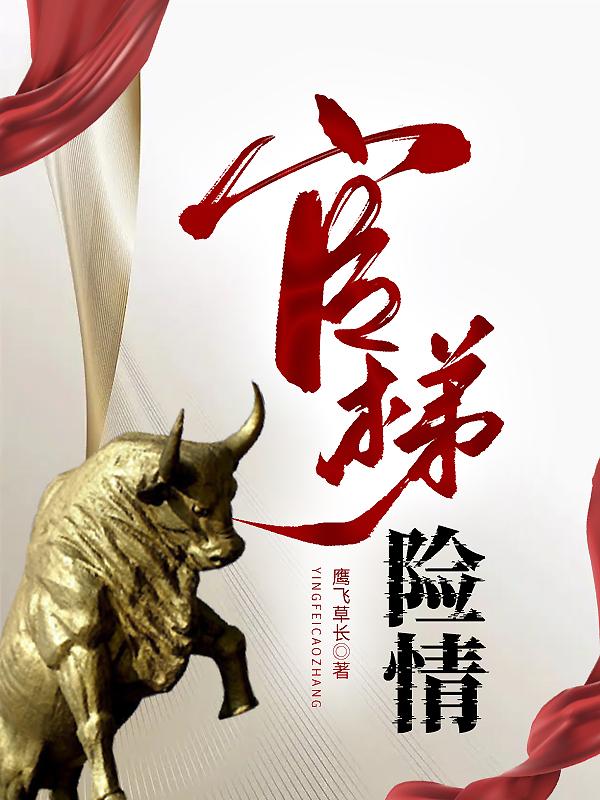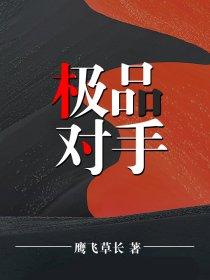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汉 母后我不想努力了 > 132140(第18页)
132140(第18页)
在信的末尾,冯三写道,新一轮材官选拔要开始了,兄长不如携家前来长安。有他在旁照料,加上兄长这么好的武艺,选不上才是怪事!
——落款,冯唐。
字里行间,透出浅浅的期待,魏尚顿了顿,高兴的情绪不减,心绪却不宁起来。
人往高处走,大丈夫谁人不想建功立业?冯唐的建议叫他心动,可他走之后,水头寨就少了一个冲在前方御敌的人。他曾发过誓,必将以匈奴的血肉祭奠双亲,倘若他一走,蛮夷再次入寨劫掠,他永不能释怀!
虽说当了材官,也许会前往边塞历练,回归云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魏尚无法去赌——赌这段时间需要多久。
他不舍地折好信,婉拒的决心坚定。
良久苦笑一声,他魏二唯一对不住的只有妻儿了。
察觉到丈夫心绪的波动,魏妻站在一旁,覆住他的手,默默表示支持。
正准备与妻子坦白,忽然间,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二郎,有旅人进了寨子,说要借宿一晚。”
魏尚的气息霎时变了:“旅人?是不是混进来的匈奴人?”
水门寨乃数一数二的边塞大寨,大汉与匈奴签订的和平协议,和平不到他们这里。时不时小规模劫掠也就罢了,数年前,竟是有会说汉话的匈奴人摸进寨子,将粮库铁库探听得一清二楚,魏尚每每想起,牙都快咬碎。
那人忙道:“不像!所以喊你去看看。”
魏尚是被筛选出来,千里挑一的牛官,与此同时会读书认字,拉得一手好弓,寨子里的青年人都极信服他。他整了整衣襟,匆匆出了门,终于知道来报信的同伴为什么说“不像”了——
他和一个七八岁的小童对上了视线。
小童长得极为讨喜,眼睛亮而圆,即便粗制衣衫也遮不住出色的样貌,此时认认真真打量着他,似在沉思着什么。
魏尚:“?”
除却寨里土生土长的孩子,从没有外人前来借宿,还带着自家年幼的儿孙的,因为此地毗邻草原,有匈奴劫掠之险。
往后一瞧,路旁摆着行囊,有两个长辈模样的人跟在小童身边。
魏尚从未见过气质如此出众的长辈,一个如同皎月,一个斐然含笑——姑且算他们是读书人好了。
他下意识尊敬了几分,问道:“几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水门寨不拒借宿,却要支付宿费,况且这里离匈奴太近了,还请几位落脚一晚,趁早回到郡中。往南走便是。”
魏尚一边说,目光总会飘到两个长辈身上。他并不是大字不识的纯武夫,停了停,忍不住笑道:“是小子冒犯。倘若留侯在此,怕也就是先生这般模样吧。”
刘越:“……”
陈平:“……”
陈平嘶了一声,这个人高马大的青年眼神不错。
转念一想,为什么是留侯在此?他曲逆侯怎么就没有姓名了?
张良诧异一瞬,温和道:“不敢。请问后生名讳?”
魏尚道:“我名尚,《尚书》的尚,魏家二郎。”
刘越左手揣右手,不知不觉念起前世背过的名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那是末世一片绝望之中,罕见地能够鼓舞人类的诗篇。梁王殿下嘀咕得极轻,哪知魏尚有个并不平凡的技能——耳力超绝,他能听到很远传来的马蹄声,由此躲过许多回劫掠,也让水头寨能够充分准备,避免被屠。
魏尚浑身一凛:“冯唐?这位小郎君认识冯唐?”
小郎君念出来的语句虽然奇怪,却自有一股雄浑的气势,不知为何,让他想要落下泪来。
魏尚双目炯炯地看向刘越。
刘越:“…………”
他自我反省,许是出门太久了,飘了,他实在对不住东坡先生。
刘越不说话,用真诚的视线望着魏尚,见逃不过去,连陈师傅都投来了怀疑的目光,这才慢吞吞地道:“家兄……算是冯唐的故人,他同我提过一句,说冯材官出生在代郡,幼时于云中边塞长居。”
“……”陈平捏了捏手,冯唐的出身经历,曾摆在过长信宫的案头,大王想必就是那时候阅看的。
与天子成为故人,真是冯唐的福气呐。
“材官”二字一出,魏尚却信了八成。他大为感慨,感叹世上缘分的巧合:“原来小郎君是从长安来,还与冯三有旧。冯三这人,正巧是我幼时玩伴,我与他形影不离,如今却已多年未见了。”
好,没错了,此人就是未来的云中郡守魏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