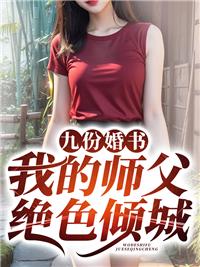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577章 下一个轮到谁(第3页)
第1577章 下一个轮到谁(第3页)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是“纸船信箱”后台警报:
>紧急请求:编号HB-309连续七十二小时未登录,最后一次留言为“黑屋子”。地理位置锁定河北邢台某乡村小学。
他立刻联系当地教育局,得知那是一名患有重度选择性缄默症的女孩,已经三年没说过一句话。学校几次试图干预均告失败,家长几乎放弃。
林小满决定亲赴现场。
出发前夜,他整理行李,阿枝默默帮他叠衣服。忽然,她拿起觉醒笔,在本子上写道:
>这次……让我跟你一起去。
他惊讶地看着她:“你确定吗?那是很远的地方。”
她点头,目光清澈:“我也……想学会听别人说话。”
第二天清晨,两人踏上旅途。火车穿过平原,掠过河流,窗外风景不断变换。阿枝靠在座位上,第一次离开高原,眼中既有紧张,也有藏不住的好奇。她掏出小本子,画下沿途所见:飞驰的电线杆、田野里的稻草人、隧道口忽明忽暗的光。
抵达邢台那天,天空阴沉。小学建在村头,外墙斑驳,操场上杂草丛生。校长苦笑着摇头:“那孩子整天躲在图书室角落,谁靠近就发抖。心理老师去了三次,都被她用书砸了出来。”
林小满没有贸然行动。他和阿枝在校园里静静待了两天,只是看书、画画、陪其他孩子做游戏。第三天下午,图书室门悄悄开了一条缝。一个小脑袋探出来,目光落在阿枝手中的彩色铅笔上。
阿枝不动声色,继续画她的画:一座山,一条河,一只纸船缓缓驶向海平面。
片刻后,女孩蹑手蹑脚走了出来,在离她们三米远的位置坐下,偷偷盯着画纸。
阿枝抬起头,对她笑了笑,然后轻轻推过一支绿色蜡笔。
女孩僵住,许久,才颤抖着伸手接过。
那一晚,她留在了图书室,画了整整三十张画。最后一张上,是一座漆黑的房子,房顶破了个洞,阳光从中倾泻而下。角落里写着两个字:
>救我。
林小满看着扫描件,心如刀割。他终于明白“黑屋子”是什么意思??那是她内心世界的隐喻,也是她唯一能描述创伤的语言。
接下来的日子,他和阿枝轮流陪伴。不追问,不逼迫,只是存在。有时一起拼图,有时涂鸦,有时单纯地并肩坐着。直到某天清晨,女孩主动递给阿枝一张新画:两个人牵着手走出黑屋,背后是漫天星辰。
阿枝红着眼眶,握住她的手,在纸上写下:
>我也怕过。但现在,我们一起亮起来。
一个月后,女孩第一次开口,声音沙哑得像锈住的门轴:
“谢……谢。”
林小满没有欢呼,没有拍照,只是轻轻说:“欢迎回来。”
返程火车上,阿枝靠在他肩头睡着了。窗外暮色四合,铁轨延伸向未知远方。他打开手机,看到桑杰发来的最新日记图片:一张照片,船长趴在窗台上,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配文是:
>今天下了场大雨。船长说,雨滴敲在屋顶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轻轻敲门。
>我想,那是大海在回应我们。
林小满笑了,眼角泛光。
他知道,这个世界依然充满误解与偏见,仍有无数孩子蜷缩在黑暗角落,用烧焦的铅笔、破碎的音节、无人理解的动作,苦苦挣扎着发出微弱信号。
但他也知道,有一艘纸船,正载着千万种声音,静静漂向黎明。
只要还有人在等,在听,在愿意蹲下来凝视那些被忽略的痕迹??
光,就会一直蔓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