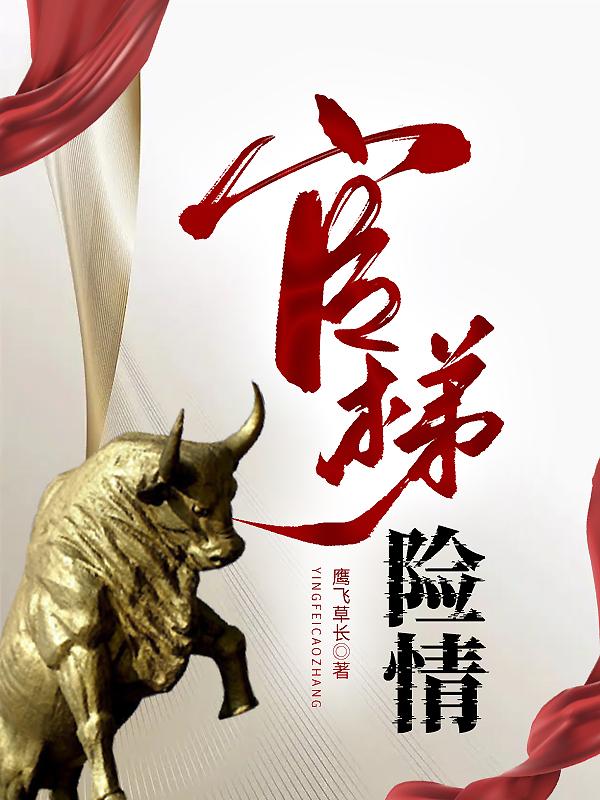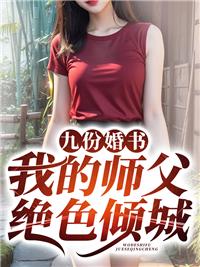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学霸的军工科研系统 > 第1623章 突破阿贝极限(第2页)
第1623章 突破阿贝极限(第2页)
“明白。”
随着栾文杰一行人的离去,实验室恢复了原本的安静。
常浩南走到“光刃”旁,轻轻摩挲着操作面板,仿佛在与它对话。
“你觉得他看得懂吗?”张汝宁凑过来问。
“懂不懂不重要。”常浩南淡淡一笑,“重要的是,他知道该怎么讲。”
张汝宁一愣,随即也笑了。
……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首都某栋大楼内,一份由栾文杰亲自撰写的内部报告正被送往更高层。
报告标题赫然写着:
《关于我国半导体产业核心技术突破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的战略建议》
正文第一段写道:
>“当前全球半导体行业正处于剧烈变革期,硅基CMOS工艺逼近物理极限,传统制程微缩路径逐渐失效。在此背景下,我国科研团队已取得多项关键突破,包括但不限于:30nm级光刻实验平台的搭建、基于ArF-193nm系统的双重曝光工艺验证、以及面向未来10nm以下节点的‘光刃’原型机研制……”
报告末尾,一段总结性陈述尤为引人注目:
>“综上所述,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制程研发体系,并展现出向更高端领域迈进的能力。建议尽快启动‘新一代光刻技术专项攻关计划’,集中优势资源,推动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化、从技术验证走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跃迁。”
文件最终落款处,一枚红色印章缓缓盖下。
……
数日后,一场秘密会议在京召开。
参会人员包括工信部、科技部、中科院、华芯国际、中电科等多家单位的核心代表。
会议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
最终,一项名为“星火计划”的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正式启动。
目标明确而坚定:
**在2030年前,实现国产高端光刻机和先进制程芯片的全面突破。**
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一片刻着“F”字的晶圆,和那台简陋却充满希望的“光刃”。
“栾主任,这份报告我大概看了一下。”常浩南一边翻阅着刚刚整理好的数据文档,一边说道,“您觉得上面会怎么反应?”
栾文杰沉吟片刻,缓缓开口:“说实话,我不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的成果已经足够引起重视。”
张汝宁在一旁插话道:“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后续的资源支持和政策衔接。‘光刃’项目虽然只是一个原型机,但它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在未来三年内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化的跨越,那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绕开现有的国际技术封锁体系。”
“这正是你们的价值所在。”栾文杰点头,“不过你也知道,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往往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成本、时间窗口、产业配套……这些都会影响最终的选择。”
“所以我们也做了两手准备。”常浩南翻开手中的资料,指着其中一页说,“如果‘光刃’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量产化突破,那我们就继续深耕ArF-1800系统的技术优化,争取用双重曝光工艺把30nm节点做到极致。同时,我们也在同步推进先进封装和异构集成方向的研究,确保即便在制程上落后于人,也能通过系统级创新弥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