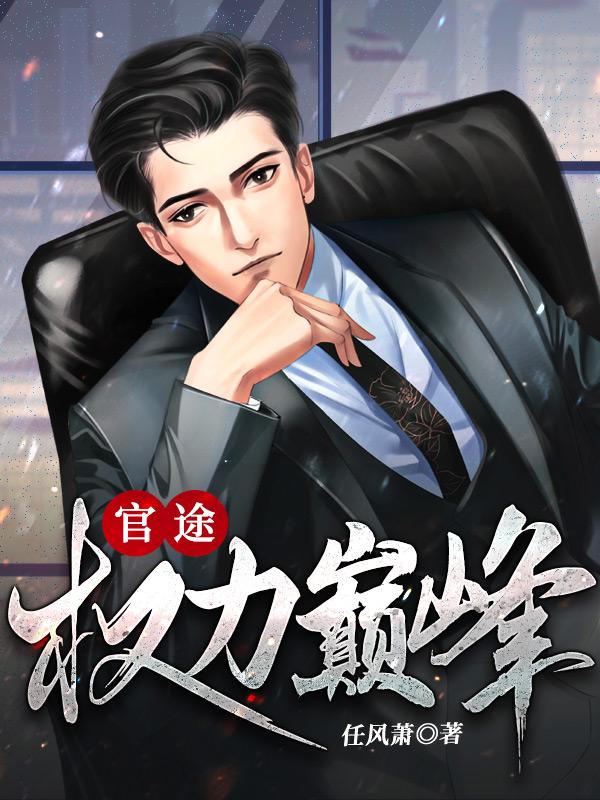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我讲烛影斧声,赵光义你哭什么? > 第157章 得知真相赵匡胤眼泪流下来(第1页)
第157章 得知真相赵匡胤眼泪流下来(第1页)
“当宗泽在得知金军胁迫赵佶,赵桓二人北去的消息时,他立即领兵奔赴滑州,经过黎阳,到达大名。
想直接渡过黄河,控扼金军的退路,截回他们两个。
只不过,宗泽的这个想法并没有成真。
因为只。。。
林昭把那枚铜铃从书包夹层里拿出来的时候,阳光正斜斜地穿过教室的窗棂,在课桌上投下一道金线。铜铃静静躺在他掌心,锈迹斑斑,边缘已被摩挲得光滑如玉。他低头看着那两个模糊的小字:“守陵”,忽然觉得胸口一闷,仿佛有谁在远处呼唤他的名字,声音低沉而遥远,像风掠过枯井。
他没在意,只当是昨晚发烧未愈的后遗症。自从一个月前那次高烧之后,他总会在梦中看见一座深不见底的石井,井底燃着幽蓝火焰,一柄青铜小斧悬浮其上,斧刃滴落的不是血,而是光。每次醒来,枕头都湿透了,像是哭过一场。
“林昭,发什么呆?”同桌推了他一把,“物理作业写完了吗?老张说今天要抽查。”
“快了。”他收起铜铃,塞进校服口袋,翻开笔记本。可笔尖刚触到纸面,一阵剧烈的耳鸣骤然袭来,眼前的文字扭曲成波浪形,耳边响起低语??
**“时辰到了。”**
他猛地抬头,教室依旧安静,窗外鸟鸣清脆,同学低头奋笔疾书。但那声音还在,如同从地底渗出,带着千年尘埃的重量。
放学后,他独自绕道去了城西的老图书馆。那里藏有一部明代《汴京志》,是他偶然翻到的,其中一页提到“守陵人”三字,后面还有一行小注:“凡持铃者,皆为始源之选,代代隐于民间,待命而启。”
他不信鬼神,却无法解释为何自己会在这本书被封存三十年后恰好找到它;也无法解释为何每当月圆之夜,家里的老式挂钟总会停摆七分钟,分秒不差。
今晚又是十五。
夜幕降临,林昭骑车穿过空旷的街道,风迎面吹来,带着初春微寒的气息。路过孤儿院旧址时,他停下脚步。那片青瓦屋早已改建为社区中心,唯有那棵老槐树还在,枝干虬曲,影子在地上摊开如蛛网。
他蹲在树根旁,掏出铜铃,轻轻摇了一下。
没有声音。
可就在那一刻,地下传来极轻微的震动,像是某种机械苏醒的脉搏。他怔住,手指颤抖着抚过铃身,忽然发现内壁刻着一行极细的铭文,肉眼几乎看不见:
**“若见衔尾蛇,即知灯将熄。”**
他心头一震。衔尾蛇?那不是前几天美术课上老师讲的古老符号吗?首尾相接,象征永恒轮回……可为什么会在铜铃上?
他正欲细看,手机突然震动。一条匿名短信跳了出来:
【别回学校宿舍。他们已经在等你。】
林昭猛地站起,环顾四周。街灯昏黄,行人寥寥。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拐角,车窗贴膜极深,看不出里面的人。他本能地后退几步,转身就跑。
回到家??其实是租住的一间小阁楼??他反锁房门,拉上窗帘,打开电脑搜索“执灯者”“始源之井”“赵怀安”。结果大多被屏蔽,只有零星论坛帖子残留着片段信息:
>“十年前有个叫赵怀安的人,在明心讲舍公开揭露‘烛影斧声’真相……后来消失了。”
>“据说他是第七代执灯者,拒绝继续供能,导致灯进入休眠状态。”
>“但灯不会死,只会沉睡。等到新容器觉醒,它就会回来。”
林昭盯着屏幕,心跳加速。他点开一段模糊视频:一个男人站在废墟前讲话,背景是一座坍塌的青铜门阵。画面抖动,音质极差,但他听清了一句:
**“真正的光明,不该来自一口吞噬生命的井。”**
那是赵怀安的声音。
他猛然想起什么,翻出小时候的照片。一张泛黄合影里,养母抱着襁褓中的他站在祠堂门口,身后香炉袅袅升起一缕青烟,形状竟与衔尾蛇惊人相似。
“难道……我不是普通孤儿?”
他抓起背包,准备离开。可刚拉开门,楼下传来脚步声,缓慢、稳定,每一步间隔精确得如同钟摆。他屏息贴墙,听见有人轻声说:
“他在上面。气息波动已匹配,α脑波频率与始源共振曲线一致。”
是两个人。穿的是便装,但腰间鼓起的轮廓暴露了武器的存在。他们说话方式冰冷机械,不像警察,也不像黑帮。
林昭迅速翻窗而出,顺着排水管滑下,落地时崴了脚,强忍疼痛钻入巷子深处。他知道自己逃不远,这些人能找到他,说明早就在监视。
他必须找人帮忙。
脑海中闪过一个名字:沈璃。
网络上关于她的信息更少,只有一条学术论文署名记录,隶属敦煌研究院古文献修复组。他试着发了封加密邮件,附上铜铃照片和那段铭文,按下发送键的瞬间,电脑自动关机,硬盘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像是被远程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