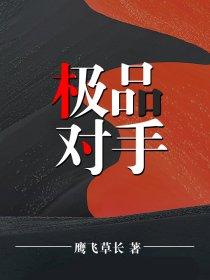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从柯南开始肝成救世主 > 第383章 时间守护者双倍月票求月票(第2页)
第383章 时间守护者双倍月票求月票(第2页)
是的,韦伯早就发现面板上关于天赋的介绍,有许多模糊或者省略的地方。
比如“更容易发现一些他人觉察不到的细节”这句。
这无疑是【鉴识眼】的效果。
那么问题来了。
它的起效的方式,会是怎样呢?
如果非要找一个最为真切的形容。
韦伯觉得应该是——
时间。
如果说,韦伯之前对于rider的“鉴识”,还能用这是因为他对于rider有许多了解来解释。
那么对于那名司机,对于那些设备甚至是自己所处的环境,又该怎么“鉴识”呢?
知晓变化需要进行比较,而比较的对象则必须是“事物的过去”。
因此,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自己才是“初次见到”,那么这种比较的前提又是从何而来呢?
“所以,自己进行对比的对象,实际上是早已被见证过的事物,或者说,是一开始就那些存在的时间本身。”
——在对自己进行“鉴识”后,韦伯清晰地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无疑是上帝的伟力。
而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起点,历史则是智慧诞生的源头。
而就像韦伯刚刚说得,因为自己的鉴识的对象是“时间”本身。
因此,用【鉴识眼】来观察“死者”是一种很奇特的感受。
……
“在这双眼睛面前,说谎、辩解……一切多余的举动,都是没有意义的。”
韦伯在心里对自己说。
“除非,凶手能瞒过时间本身,以及,我恰好能在参加的第一个案件里,遇上这种可怕的情况。”
就比如——
他现在看到的“间桐脏砚之死”。
刀光。
很快的刀光。
于夜光下闪着寒芒,透着冷意,一击便刺透胸膛,分开那老朽的心脏。
然后,温暖的血液便喷洒在庭院的草坪上,和那些微凉的夜露混杂在一起。
但韦伯却很清楚,间桐脏砚不是这样死的。
甚至,随着目暮警官而来的法医,早已给出了这个老人死亡的原因。
“凶手应当是一刀封喉将死者封喉,避免他发出求救声,然后才在死者的胸口补了一刀。”
“但不是这样的。”韦伯在心里说,“死者是在死后,被凶手转移到前厅的。”
韦伯的目光落在间桐脏砚的衣服的袖口处,一些不自然的深黑色痕迹,在袖口的纽扣内。
衣服上的泥土痕迹,可以很轻易地通过拍打除去,但是那些因为挤压,塞满缝隙的泥土不行。
但真实的死因,又的确是因为脖子上的血痕。
甚至,刚才自己和rider就从草坪外的道路上经过。
从自己看到的痕迹来看,喷溅在草坪上的血液,根本不可能被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