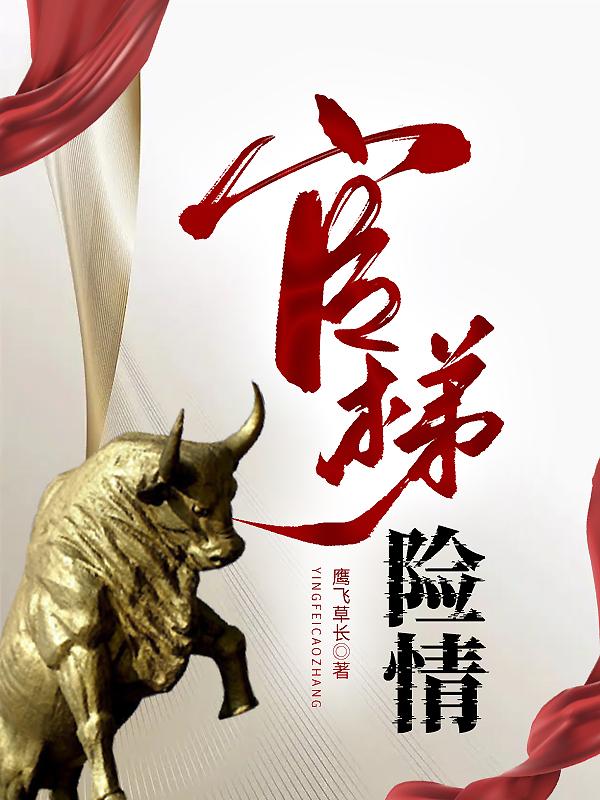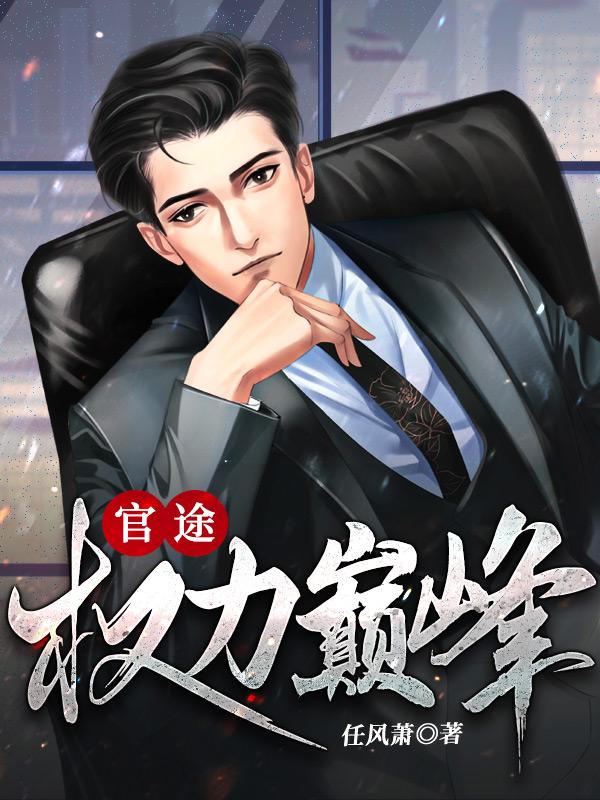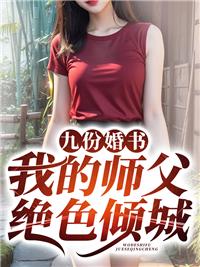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62章 到首辅府拿人(第1页)
第462章 到首辅府拿人(第1页)
此时,黄千浒手中正翻阅着一本看似不新不旧的手札。
说它不新,是因为手札的纸张边缘已显磨损,显然时常翻阅。说它不旧,是因为其缝线尚且完好,内里的墨迹也依旧清晰。
约莫半月前,这位权倾朝野的首辅大人手中便多了这本手札,无人知晓其内容。
若有心人能够凑近细看,便会发现,手札开篇赫然抄录着凌川当日曾言的‘乾坤四训’。往后翻去,则是那篇惊世骇俗的《水舟论》,以及凌川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诸多独。。。。。。
风雪又起时,已是三年之后。归语村的蓝莲花开得比往年更盛,一丛丛从石缝里钻出,像是大地深处不肯熄灭的火焰。那柄铁铲仍立在屋檐下,只是木柄已有些朽坏,被村民用红绳仔细缠了几圈,如同供奉一件圣物。可谁都知道,它从来不是用来敬神的,而是属于一个会冷、会累、会痛,却从不回头的人。
柳芸老了。她的发间已有霜色,眼角刻着岁月的细纹,但眼神依旧清明如初。忆学馆早已不再只是一座藏书之所,而成了遍布边关十九驿的记忆驿站。每一名新入馆的弟子,第一课便是背诵《守路日记》中的那一句:“我不想当英雄,我只是怕忘。”第二课,则是亲手抄写《边民纪实》中的一篇故事,无论多平凡,都必须一字不落。
这一日清晨,她正坐在院中晒太阳,手中摩挲着那枚锈蚀的铜扣。忽然,远处传来马蹄声,急促而沉重。一名年轻驿卒翻身下马,脸色苍白,递上一封火漆封印的信。
“长安急报,修史局……出事了。”
柳芸缓缓拆信,指尖微微发颤。信中只寥寥数语:**“野闻录重刊,陈七事迹被篡为‘天授兵法,夜斩千敌’,民间再起建庙之议。长老抗争未果,昨夜暴卒。群儒噤声,唯忆学馆尚存一线呼声。”**
她闭上眼,良久未动。风穿过庭院,吹动檐下的铜铃残片,发出一声轻响,仿佛是谁在低语。
“终究还是来了。”她喃喃道,“只要人心贪恋神明,真实便永无安身之地。”
当晚,柳芸召集所有弟子于万忆塔旧址。无名碑前燃起九盏油灯,象征九种记忆的形态:口述、手稿、器物、图像、歌谣、碑刻、梦境、遗言、沉默。她站在碑前,声音不高,却穿透寒夜:
“今日我们不讲道理,只问一事:你们是否还记得陈七的模样?不是庙里金身披甲、手持长枪的战神,而是那个蹲在雪地里,一边啃冷馍一边默默铲雪的男人?”
众人默然。片刻后,一名来自北境的女弟子低声开口:“我父亲曾是修路队的工头。他说,有一年大雪封山,粮草断绝,陈七把自己那份省下来,悄悄塞进伤病员的铺盖里。他自己饿得晕倒在路边,被人抬回来时,嘴里还含着半块冻硬的窝头。”
另一人接道:“我在西驿查档时发现,每年冬至,都有匿名送来的炭薪和粗布,登记簿上写着‘陈七旧部’。可那些名字,大多已在战报中‘阵亡’多年。”
又一人道:“我去过心渊峡谷。当地人说,每逢月圆之夜,若静听风声,能听见铲子刮石的声音,还有人低声哼一首不成调的小曲??那是阿音最爱唱的《归语谣》。”
柳芸听着,眼中泛起水光。她取出一只陶罐,正是当年福建渔村那孩子埋下的那只,如今已被考古者寻回,罐内画纸尚存,虽已泛黄脆裂,但两个小人依稀可见,一个拿铲,一个牵线。
“这就是记忆。”她说,“它不在朝廷的卷宗里,不在文人的诗赋中,而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痕迹里。它们像种子,落在荒原,看似死去,实则等待春风。”
她将陶罐置于碑前,点燃一支香。“明日我将启程赴长安。若他们执意造神,那我就亲自拆庙。”
三日后,长安城外。一辆朴素的牛车缓缓驶入皇城南门,车上坐着一位白发妇人,怀抱一只木箱,箱上贴着三张封条:**“伪物辨”、“真迹考”、“守诺证”**。守门禁军欲拦,却被随行太监认出身份,连忙放行。
朝堂之上,正值修史局呈献新编《国史?忠烈传》。主笔大臣慷慨陈词:“陈七乃天赐将才,率孤军守边三十年,斩敌十万,筑长城千里,更有神鸟护体、雷火助战之异象……此等人物,岂能仅列‘民德’?当入‘英烈’,享万世香火!”
话音未落,殿外传来一声清越的叩击声。
众人回首,只见柳芸拄杖而入,身后两名弟子抬着木箱。她直行至御阶之下,不跪不拜,只将箱打开,逐一陈列:
第一件,是一具残破铠甲,胸前有焦痕与刀劈裂口。“此为陈七最后一战所穿。据幸存老兵回忆,他并未骑马冲锋,而是步行断后,掩护伤员撤离。此甲重达三十余斤,他带伤负之行走七日,终力竭倒地。所谓‘夜斩千敌’,实为七人围攻,死战方退。”
第二件,是一册残页兵书,墨迹斑驳。“此即所谓‘天授兵法’原本。经多位学者比对,内容实为前朝《戍边策》节选,且多处批注出自他人之手。真正由陈七亲撰者,唯一页纸:‘遇伏勿躁,先察风向;补给优先,胜败次之。’十六字而已。”
第三件,最令人动容??一块布满划痕的石板,上面密密麻麻刻着数百个名字,每个名字旁标注日期、地点、死因。“这是他在每一场战役后亲手记录的阵亡者名录。他曾说:‘我不记功劳,只记谁没能回家。’而这名单,从未上报朝廷。”
满殿寂静。
皇帝凝视良久,终问:“你为何如此执着?即便他不愿被铭记,你也非要撕碎世人对他的敬仰?”
柳芸抬头,目光如炬:“因为我记得他真正的愿望。他不要香火,不要神话,不要万人高呼他的名字。他只要这条路还在,只要有人走过它时不觉得孤单。可如今你们把他变成一座庙,把他的名字变成咒语,让百姓烧香求胜、求财、求子,这难道不是对他一生的背叛?”
她顿了顿,声音渐沉:“你们以为是在尊崇他,其实是在杀死他。真实的他已经死了,但虚假的‘陈七’却越活越久,吞噬一切。而那些真正活过、苦过、死过的人呢?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血,都被埋进了这座虚妄的丰碑之下。”
殿内无人应答。
皇帝起身离座,亲自走下台阶,拾起那页十六字兵法,反复摩挲。良久,他下令:“《忠烈传》暂缓刊行。野闻录另册存档,注明‘未经核实’。陈七事迹,仍归‘民德卷’,标题不变:‘守诺者’。”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一些地方已建成的“陈七庙”被迫改名“边民祠”,供奉对象变为无名戍卒群体。有狂热信徒焚香抗议,甚至有人夜闯忆学馆欲毁《守路日记》,却被一群自发守护的老兵拦住。
其中一人,正是当年怒闯忆学馆的老兵。他已须发皆白,拄着拐杖站在门前,冷冷道:“你们拜的若是战神,那就去拜吧。但别用他的名字。他不是你们口中那个无所不能的神,他是个人,一个答应了事情就做到死的人。我见过他流血,见过他哭,见过他抱着战友尸体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样的人,不需要你们造神来荣耀他。”
风波渐息,柳芸却未归。她在长安停留数月,主持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记忆审定大会”。各地送来声称与陈七有关的遗物共计三百二十七件,经考证,仅十二件可信,其余皆为伪造或误传。她命人将真品编目入库,伪物则集中焚毁,灰烬撒入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