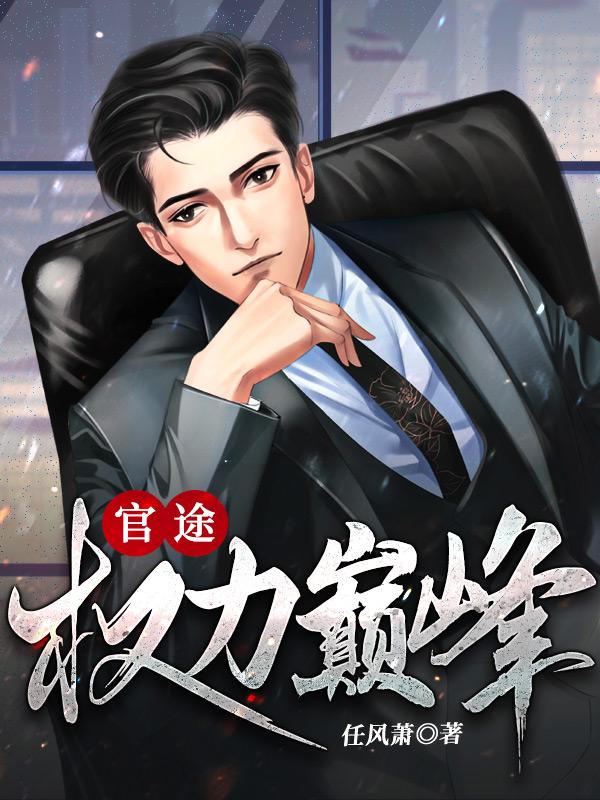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步步登阶 > 第521章 三个字的(第2页)
第521章 三个字的(第2页)
我心头一震。那张照片摄于1998年育音谷周年纪念合影,后排右三站着一名戴眼镜的男人,肩章标识为“心理评估组副主管”。根据早先档案,此人名为陈允明,应在2005年因车祸死亡。但照片下方打印的一行备注让我血液凝固:
>**身份核实进展:该人现用名林志远,持有新加坡籍,近三年频繁出入东南亚多国难民营,职务为‘心理健康顾问’。**
也就是说,当年参与初代实验的核心成员,不仅未被清除,反而以全新身份渗透进新一代弱势群体之中。他们借着“援助”之名,继续布设认知陷阱,甚至可能正在培养下一波缓冲层儿童。
我立刻拨通许小阳电话。“你父亲的日志里有没有提过这个人?”
“有。”他的声音透着疲惫,“陈允明是他最信任的助手,也是第一个主张使用‘情感剥离诵读法’的人。他说,只要让孩子相信谎言比真相更安全,他们就会自愿封口。”
“而现在,他回来了。”
“不,”许小阳低声道,“他从未离开。他只是换了舞台。”
三天后,我们召开紧急线上会议。七人全部上线,画面分割成七个方格,分布在不同大陆的深夜与黎明之间。E-7展示了最新追踪成果:通过比对难民学校监控录像中的语音节奏,他们锁定了至少六名疑似前研究员的活动轨迹,全都集中在赤道附近气候湿热区域??那里常年云层厚重,卫星监测盲区密集,正是理想的信号屏蔽地带。
“他们在重建网络。”E-7说,“不是为了延续旧系统,而是要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替代版本??没有中枢节点,每个孩子都是接收器兼发射器,形成自我维持的情感压抑生态。”
许小阳忽然开口:“我能联系到我爸的老同事。有些人当年虽签了协议,但也偷偷留了后路。如果能拿到原始设计图纸,或许能找到强制关闭所有备用节点的终极指令。”
“风险太大。”张晓雯反对,“你现在已是公众人物,任何异常接触都会被监控。而且……你确定自己准备好面对他了吗?”
许小阳沉默片刻,眼神却愈发坚定:“我不是为了原谅他。我是为了终结他亲手造出的怪物。”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坐在灯下,打开一封刚收到的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模糊的家庭录像,拍摄时间标注为2003年秋。画面中,一个小男孩坐在沙发上背诵课文,母亲在一旁微笑鼓掌。镜头晃动了一下,扫过茶几上的日历??日期旁用红笔圈出两个字:“静默”。
接着,男童突然停下,抬头问:“妈妈,为什么老师让我们每天说三遍‘我没受伤’?我真的没受伤吗?”
母亲笑容僵住,随即温柔地说:“因为这样,坏事情就不会来找我们啦。”
男孩低下头,再次朗读:“我没受伤,我没有痛苦,我不需要帮助。”
每说一句,眼睛就闭一下,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视频最后几秒,镜头无意拍到了门外阴影里的男人轮廓。他穿着白大褂,手中握着记录板,左手腕处露出一小截蛇形胎记。
我全身冰冷。那是周振国。他不仅主导高层决策,还亲自参与基层实验执行。这意味着,整个体系的残酷性并非“误用”或“失控”,而是自上而下的精密设计。
那一夜,我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巨大的地下图书馆中,四壁摆满磁带与硬盘,每一盒标签上都写着一个名字。当我抽出其中一卷播放,听到的却是自己的声音在重复那句咒语般的口号:“我没有看见任何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需要说出来。”
我拼命想喊停,却发现嘴巴无法张开。直到远处传来一声稚嫩的呼唤:“叔叔,你能帮我找妈妈吗?”
我转身,看见一个小女孩蹲在角落,怀里抱着一本烧焦的笔记本。她抬起头,正是录音中那个写下“风会把它带到外面”的孩子。
“你是谁?”我问。
“我是样本33。”她说,“也是第一个听见地底声音的人。”
“那你现在听见了吗?”
她点点头:“它们在等你们说完最后一句话。”
惊醒时天还未亮。我起身打开电脑,将昨夜整理的所有线索串联成一条完整证据链,命名为《静默工程全图谱》,并设定自动发布时间为七十二小时后。同时,我向公安部特别法庭提交补充证词,附上陈允明(林志远)及周振国的影像比对报告、跨国行动轨迹分析以及至少十二名幸存者的交叉指认记录。
做完这一切,我给许小阳发了条信息:“钥匙已经铸成,门由你来推。”
他回复得很快:“我已经启程去新加坡。不管他在哪里,我都得让他亲耳听见,他儿子说的是真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媒体对《育音备忘录》的报道逐渐降温,街头集会也慢慢散去。但我知道,这场战争早已转入更深的层面。在无数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人正悄悄打开尘封的日记,有人第一次向心理咨询师坦白童年阴影,有教师主动交出当年销毁的学生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