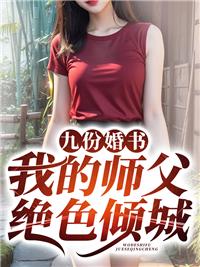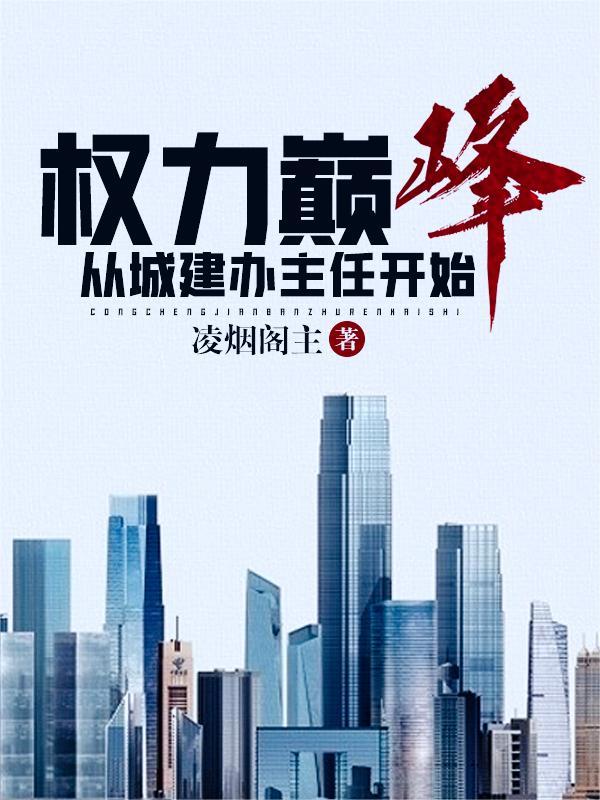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大唐:太平公主饲养指南 > 第四百九十一章 双姝(第2页)
第四百九十一章 双姝(第2页)
吐蕃高原上,僧侣们合力抬起一名冻僵的旅人,将其裹入袈裟之中;
南海渔船上,渔民将捕捞到的最后一尾鱼放归大海,说:“留给明天的孩子吧。”
最后,屏幕定格在一句话上:
>“太平不在天上,她在人间每一次温柔的选择里。”
这一夜,全球超过两亿人目睹了这段影像。没有口号,没有神迹,只有平凡中的光辉。许多人默默关闭了家中供奉的“裴景之神像”,取而代之的是一盏蓝灯、一本手抄《心盟誓约》,或仅仅是一杯清水。
伪教残余势力试图反击,散布谣言称“太平已被邪术控制”,并组织信徒冲击守梦学院分院。然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沉默顺从的群众,而是自发集结的“心引师”与普通百姓组成的防线。
在陇右一役中,三百名农妇手持竹竿,围成人墙,高唱《清平调》原曲,歌声穿透寒风,竟使进攻者纷纷放下武器,跪地痛哭。一名前伪教骨干泣诉:“我娘临终前还在背诵《心政十策》,可我却把她当成愚昧老人……”
风波渐平,秩序重建。但真正的变革,已在无声处发生。
三个月后,守梦学院发布《全球共情指数年报》。数据显示:暴力事件同比下降68%,心理疾病发病率下降54%,跨民族通婚率上升217%,儿童梦境质量连续九个月保持“稳定清明”状态。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曾经最封闭的几个村落,出现了第一批由村民自主推选的“梦语长老”??他们不通机关术,不懂咒纹,却能凭借倾听与共情化解世代积怨。
裴景之读完报告,久久无言。他站在长安城头,望着万家灯火,忽然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
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在想什么?”
他回头,见太平披着素色斗篷,手中提着一盏纸灯笼,笑意温婉。
“我在想……这一切会不会太顺利了。”他说,“历史从未如此温柔对待过理想主义者。”
太平走近,将灯笼递给他。“你看这灯,火焰微弱,随时可能熄灭。可只要有人愿意护住它,风再大,也不会灭。”
她指向远处一条小巷,那里有个老乞丐正蜷缩角落。一名少年路过,停下脚步,脱下外衣盖在他身上,又从怀中掏出半块饼,轻轻放在他手里。
“那样的人,过去也有,现在更多。”她说,“我只是让他们看见彼此。”
裴景之低头看着灯笼里的火苗,忽然问:“你会留下多久?”
太平沉默片刻,望向北方星空。“当人们不再需要我时,我就会走。或许百年,或许十年,甚至明日。”
“那你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
她笑了,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简单的问题。
“没有救世主的世界。”她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光。”
数日后,太平开始巡行天下。她不住皇宫,不乘銮驾,仅携两名侍女,徒步行走于城乡之间。她在灾民营中为孩童讲故事,在学堂里与学生辩论“何为正义”,在刑场外请求刽子手暂缓行刑,只为听完囚犯最后的愿望。
她不做评判,不颁法令,只是存在。
而她的存在本身,就成了最锋利的镜子,照见每个人的良知。
某日,行至巴蜀深山,遇一隐士。此人曾是当年伪教幕后策划者之一,事发后逃亡至此,终日闭门不出。太平执意登门拜访。
两人对坐良久,隐士终开口:“你不怕我再次掀起狂澜?”
“怕。”她说,“但我更怕你不肯说出心里的话。”
那一夜,他们谈至天明。次日清晨,隐士自愿随她前往长安受审。临行前,他在门前石碑刻下一行字:
>“执念起于孤独,破执始于被听见。”
此事传开,举国震动。连一向冷漠的史官也在《实录》中写下一句罕见评语:“公主行处,铁石开花。”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无为而治”的方式。
朝廷内部暗流汹涌。一些大臣密议:“太平虽贤,然无名分,岂可游走四方,动摇礼法?”更有宗室贵族联名上书,请立其为“女帝”,欲借其声望重振李唐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