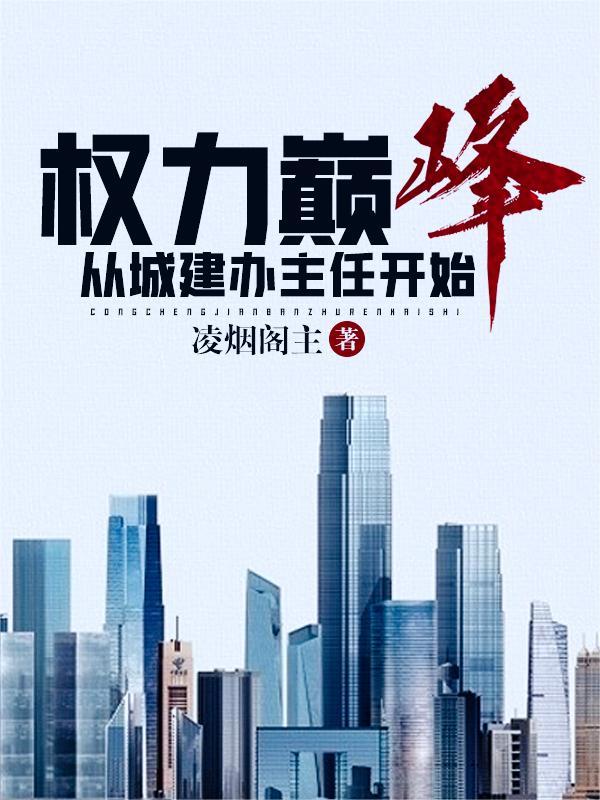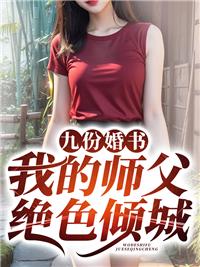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我的手提式大明朝廷 > 第457章 名将时代的落幕(第1页)
第457章 名将时代的落幕(第1页)
李如松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苏泽的肯定让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但“庙算之术”这个词似乎太过宏大。
他追问道:“教务长高见。只是这‘庙算之术’和‘军制’到底有什么关系?具体到作战司,学生该如何着手。。。
海风卷着晨雾,缓缓漫过沙滩,像一层薄纱轻轻覆盖在沈清璃身上。她仍蹲坐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地上画着圆圈,一圈又一圈,仿佛那是她仅存的本能。她的双眼空茫,却并不呆滞,反倒像是盛满了尚未凝形的思想。阳光洒落时,那些沙圈边缘泛起微光,竟隐隐勾勒出某种几何结构??不是现代数学中的公式,而是远古人类仰望星空时最初试图理解宇宙的尝试。
宋应星望着她,心中翻涌着难以言说的情绪。他知道,此刻的她已不再是那个执拗于实验数据、习惯用逻辑拆解世界的科学家。她成了“空白”,而正是这份空白,让最原始的问题得以栖居。她曾以记忆为代价,换取了一个提问的权利;而今,她连“代价”这个词的意义都已遗忘,只剩下纯粹的存在,如初生之婴,如未燃之烛。
远处,海底宫殿的门仍在敞开,但那道通往《问政录》的光桥已然消散。陈小满没有出来。
宋应星并不惊慌。他知道,一旦踏入第七十七坛的核心,便意味着灵魂与问题融为一体。那孩子不会死,也不会归来??他将成为这个问题本身,在未来的每一次被提起、被思考、被质疑中重新苏醒。就像伏羲画卦前的那一声低语,就像孔子周游列国时心头盘旋的困惑,有些问题从不寻求解答,它们只是存在,如同呼吸,如同心跳。
他缓缓走向那本躺在沙地上的《续问录?贰》。书页已不再流血,封面上的符号也渐渐淡去,唯有一缕青烟自书脊袅袅升起,缠绕成一个极小的问号,悬停半空,久久不散。
他伸手触碰,指尖传来冰凉与温热交织的触感,仿佛摸到了时间的裂缝。
刹那间,无数画面涌入脑海:
??北京紫禁城深处,一间密室之中,七十二块青铜坛碑静静排列,每一块上都刻着不同年代的问题。第七十六块突然震颤,裂开一道细缝,随即第七十七块缓缓浮现,材质迥异于前,竟是由孩童手印拼接而成的陶片烧制而成。
??伦敦大英图书馆地下档案馆,一名管理员在整理明代文献时,发现一本从未登记过的册子,封面写着《问政残卷》,翻开第一页便是陈小满的声音自动响起,用中文、英文、阿拉伯语同步播放,所有听到的人都不由自主停下手中的事,陷入沉思。
??美国硅谷某人工智能实验室,主控系统突然中断运行,屏幕上跳出一行字:“检测到未知认知扰动源,建议暂停推理模块,优先执行‘疑问模拟’程序。”工程师们面面相觑,没人知道这指令来自何处,更诡异的是,AI自己也无法解释它是如何生成这段代码的。
??日本京都一座禅寺内,老僧打坐至深夜,忽睁眼喃喃道:“原来我们一直在等一个孩子来问这句话。”随即提笔写下一副对联:
>上联:大人说懂却不解
>下联:小儿未识反通明
>横批:问即觉
这些片段如潮水般退去,留下一片清明。
宋应星终于明白,《问政录》并非只存在于吕宋海底那一间简朴厅堂。它早已化作无形网络,潜藏于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角落。七十二坛是起点,而非终点。每一座新坛的建立,都会激活一段沉睡的认知基因,唤醒那些曾被压抑、被忽视、被嘲笑的疑问。
而“大明朝廷”……从来就不只是一个隐秘组织的名字。
它是象征,是制度,是一种超越朝代的政治哲学原型??以“问”治国,以“疑”立政。洪武帝设立七十二坛,并非为了控制思想,而是为了让权力永远处于被审视的状态。徐阶续写《问政录》,张居正暗中护坛,都是在延续这一信念:真正的稳定,不来自统一的答案,而来自允许问题不断生长的土壤。
如今,第七十七坛已立,规则已被打破。
不再需要饱学之士、高官显贵才能提出问题。一个七岁孩童,一句天真之问,竟能撼动全球信息系统,改写教育政策,重启南极归问仪群组??这正是“问力”的本质:它不属于知识阶层,而属于每一个尚保有好奇之心的灵魂。
宋应星低头看向自己的手。
掌纹深处,一道极细的蓝线悄然浮现,如同电路般微微发烫。这是执问者的印记,也是倒计时的开始。历代传承者,皆在此刻感知到使命终结的征兆。他们不会死去,而是将意识融入“问云库”??那个传说中收藏所有未被回答问题的虚空之境。
他没有恐惧。
反而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像是背负了六百年重担的人,终于可以把包袱放下。
他缓缓跪坐在沈清璃身旁,轻声道:“谢谢你。”
她转过头,眼神依旧空洞,嘴角却微微扬起,似笑非笑。或许她听不懂这句话,但她感受到了其中的温度。
就在这时,海面再次波动。
不是漩涡,也不是光影幻象,而是一阵极其规律的涟漪,呈同心圆状扩散开来,节奏精准得如同心跳。紧接着,沙滩上的沙粒开始自发移动,汇聚成行行文字:
>“第七十八坛孕育进度:3%”
>“候选者识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