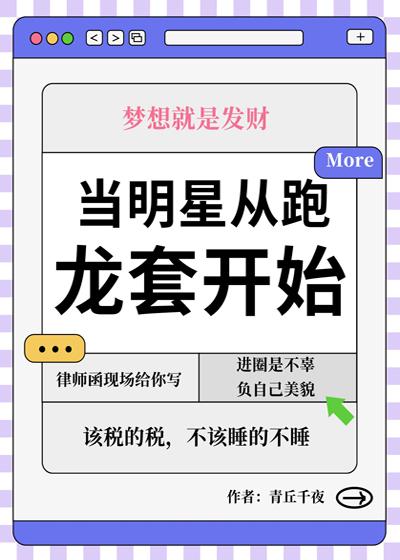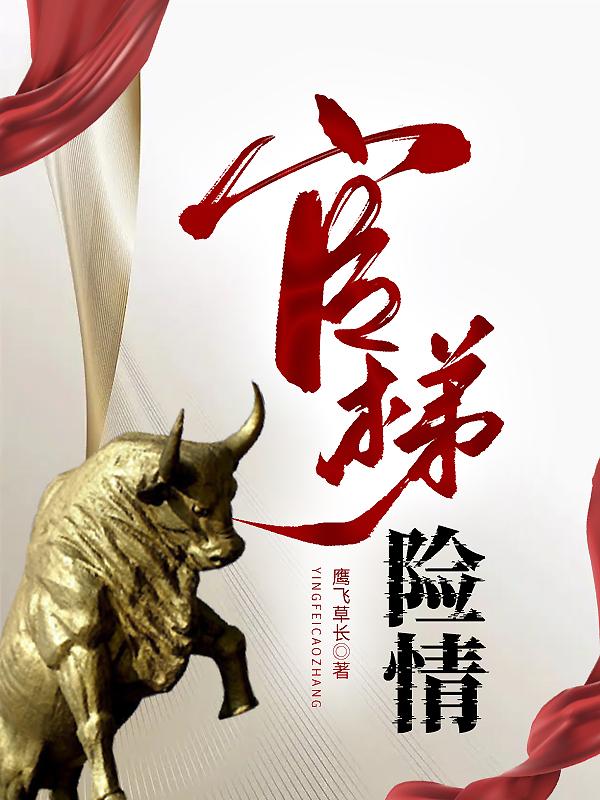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流民她青史留名 > 封侯(第4页)
封侯(第4页)
“为君之道。”
。
永昌九年,长安。
满是药味的御书房内只留了两盏灯,烛火昏暗。近年来皇帝的目力越来越差,稍微亮一些的光都会刺得她双眼发疼。
她躺在龙榻上,手里捏着密报,没有打开,疲惫地摆摆手:“你直接说罢。”
“戎州有一人,肖似故太子李明允。”薛宛躬身回话,一身绯色官袍衬得身姿挺拔。
她虽说着肖似,但以她的性格,若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拿到御前来说。
皇帝直起身,面上一瞬间闪过欣喜,拉住薛宛的手:“恒儿?他还活着?”
“回陛下,正是。”
皇帝看着薛宛匍匐的脊背,短暂的欣喜飞快散去,逐渐年迈的思维还是很快反应过来:“他还活着,那为什么还瞒着我,悄悄躲在蜀地?”她冷笑,“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吗?”
薛宛平铺直述道:“据报,西南一十九州的上层官员都已知晓秦王的身份,但他们无一人上报。这其中包括楚王殿下、韩世子、戎州司药姜鹤羽,以及据说肖似已亡故的谢安的戎州司马江离。”
皇帝越听越是心惊,脸色彻底沉下来。她一把打开密报,一目十行地看完。
“肖似谢安?只怕就是谢安罢?还有姜鹤羽,我记得,她与这江离是一家人?”
薛宛低声应“是”。
“好啊,好啊!一群欺君罔上之徒!”皇帝胸口剧烈起伏,将密报掷到一边,“我的好儿子,我的恒儿!当初不是跪在御书房外赌咒发誓说自己绝不会谋反吗?那如今笼络这些势力又是在做什么?!”她喘了口气,眼里闪过一丝狠厉,“来人!传旨……”
“陛下三思!”薛宛跪在地上,膝行上前阻拦。
皇帝死死盯着这个在朝中几乎没有任何倚靠的孤臣,嘲讽道:“怎么,连你也看我老了,要另择新主了?”
“陛下,臣对陛下忠心耿耿,日月可鉴!”薛宛目光如炬。
“那你拦着朕做什么?”皇帝冷哼一声,用力甩开她的手,“朕今日就要派兵……”
“陛下!”薛宛再次抓住她的袖摆,眼中含了泪,声音也哑了下来,“西南边军有近二十万人。”
皇帝一怔,愣愣靠在床头。
良久,她忽然笑了:“依你的意思,我还动不得他了?”
薛宛沉默着,没说话。
一阵阵针扎似地疼从太阳穴开始,直直传到脑中,皇帝用力合上眼,咬牙忍过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疼痛。
等再次清醒过来,她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榻上,额上搭着温热的绸巾,榻边跪着一脸担忧的薛宛。
皇帝已经有些浑浊的双眼眨了眨,方才的怒火已然平息。她牵唇笑笑,握住薛宛的手:“朕无事。”
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么多年,她心里很清楚,薛宛的话才是对的。
赵恒已经掌控了西南,又是朝中老臣们心里当之无愧的好太子,要想镇压他的势力,并不像几年前镇压反叛军那么容易,更何况,赵恒如今并没有发兵造反。她先下手,就是失了道义。
她已经老了,如今宫里宫外心思浮动,人人都在站队,就像很多年前拥立她一样,又在为这个江山寻找一个新的主子。
她叹了口气,不知是失望还是难过,只喃喃道:“这个逆子。”
薛宛握住她的手,轻声劝说:“陛下,秦王若是想反,只怕早就反了。如今这些消息,应当是他有意放出来的,想必秦王殿下……还是惦念着母子之情。”
“什么母子之情,”皇帝自嘲一笑,“当初死了那么多人,连他自己也是死里逃生,哪会念及什么母子之情?”她看向黑漆漆的宫殿,喃喃道,“我的恒儿长进了,这是在与我打擂台呢。若是十年前,我当真会杀了他。可现在,我老啦。”
说到此处,她难以抑制重重咳嗽,几乎要将肺都咳出来。
薛宛抚着她的背,轻柔地顺着。
皇帝缓过气来,几乎是自言自语道:“老三平庸懦弱,老四心胸狭隘,老五……野心倒是不小,都舞到她娘我跟前来了,只可惜,能力太差。”她冷笑一声,“朕这几个孩子,都不堪为君。唯独这老二,从前先皇在位时就看好他,如今更是长进了,能隐忍蛰伏近十年。”
说起先皇,她脑中不可避免地又浮现出那个男人温言软语的模样。人老了,就总是忍不住惦念旧人。
皇帝合上眼,低声问:“宛儿,你说,朕要把他召回来吗?”
薛宛垂下头:“臣不知。”
“不召也不行啦。”皇帝知道她不会回答这种问题,她坐起身,趿拉上软底鞋,扶着薛宛的胳膊站起来,“难道真要等到病得下不来床的时候,眼睁睁看着他打进长安来?还不如趁现在还没撕破脸,还能多个‘孝顺’的好儿子。”皇帝笑了笑,“人啊,要服老。人家年轻人都给我递台阶了,那我还是往下走走吧。”
她缓缓走下宫阶,眉眼间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威严:“传旨,宣秦王李明允及其家眷、属官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