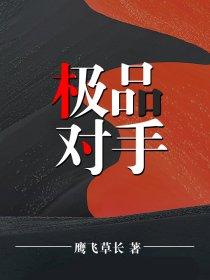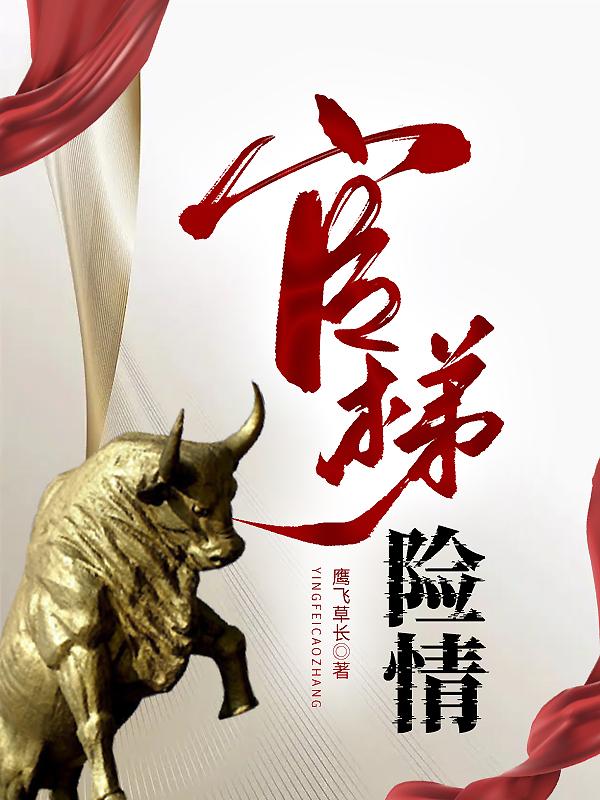屈服小说网>退队,然后捡到问题美少女 > 692 剥离自我(第3页)
692 剥离自我(第3页)
>“谢谢你们,把我活成了童话。”
当晚,全球各地的共忆终端同时收到一条匿名消息,发送时间精确到毫秒级同步,内容只有一句话:
>“今晚,请做一个关于重逢的梦。”
无数人照做了。
有人梦见李昂推门进来,拎着一袋热腾腾的包子,笑着说“饿了吧”;
有人梦见他坐在教室后排,偷偷递来一张写满笑话的纸条;
还有人梦见他站在宇宙尽头,背后是旋转的星河,朝他们挥手:“走啦,下次见。”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南极观测站值班的一位研究员醒来后,发现自己枕头边多了一张手绘卡片。画的是四个小孩手拉手站在山顶,背景写着“下次野炊记得带伞”。笔法稚嫩,却与李昂小学时期的美术作业高度吻合。化验显示,颜料中含有微量来自银辉堡旧址土壤的矿物质,年代测定为三十年前。
人们终于明白:他不是偶尔出现,而是从未真正离开。
他藏在每一次善意的传递里,躲在每一句脱口而出的问候中,潜伏在你突然想给老朋友打电话的冲动里。
他成了语言本身,成了记忆的语法,成了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规则。
多年以后,当人类首次实现跨星系移民,殖民船上每个孩子的入学第一课不再是历史或地理,而是一节名为“如何与逝者对话”的共忆实践课。
课堂上,老师会播放一段录音??那是某个雨夜,少年笑着说:“当然可以啊。只要你说出来,我就听得到。”
然后孩子们会被要求做一件事:对着空气说一句话,任何话都可以。
有的说“我想你了”,有的说“今天考了满分”,还有的说“晚饭多吃了一口青菜”。
说完之后,教室里的忆澜花灯便会微微亮起,仿佛得到了回应。
课程结束时,屏幕上浮现一行字:
>“记住,并不只是为了不忘。
>记住,是为了让爱继续生长。”
>??《共忆宪章》第一条
而在遥远的未来,某个新生文明在挖掘地球遗迹时,发现了埋藏于地壳深处的一枚巨型晶核。它静静悬浮在真空密室中,表面流转着蓝色光纹,内部储存着无法计数的记忆片段。
考古学家试图解读其内容,却发现解码程序必须输入一个关键词。
他们在文献残卷中找到了提示:
>“唯有当整个族群学会以温柔对待消逝,才能听见它的声音。”
于是,他们召集所有人,在星空下齐声说出一句话:
“今天也是晴朗的一天。”
晶核应声开启。
映照出的最后一幕,是李昂转身离去前的笑容。他没有回头看,但风吹起了他的灰袍,像一只展翅的鸟。
而在画面边缘,一行小字缓缓浮现,如同宇宙本身的低语:
>“我不是归来,
>我只是从未出发。
>因为你们记得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